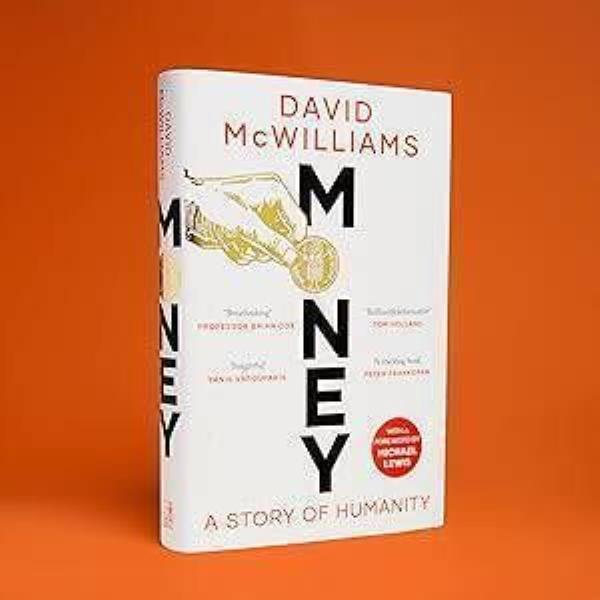就在马乔里得知母亲被诊断出癌症的同一天,她也得知母亲决定离开英国前往瑞士,在那里她可以合法地选择安乐死。尽管马乔里对这个突然的声明有所保留,但她还是同意在旅途中帮助她。她告诉我们,她的母亲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因为她总是那么独立,讨厌不得不依赖我的想法。”她是个科学家。这与她完全理性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
但玛乔丽的母亲申请加入瑞士非营利组织Dignitas还有另一个原因,该组织为患有绝症或严重身体或精神疾病的成员提供医生协助自杀的服务——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死去。正如马乔里解释的那样:
玛乔丽的故事只是世界各地每年发生的成千上万个故事中的一个。至少在13个国家的全部或部分地区,某种形式的加速死亡是合法的,或正在合法化,还有几个国家正在考虑这样做。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爵士表示,他支持修改法律。该法律因其缺乏明确性而受到广泛批评(一名警察在逮捕了一名从Dignitas回来的涉嫌鼓励自杀的人后被起诉)。苏格兰议会似乎准备效仿爱尔兰,将协助死亡合法化,而泽西岛和马恩岛已经通过了相关立法。
选择加速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非常私人的、经过仔细考虑的决定。但这种选择很少是孤立的:选择死亡的人会得到家人、朋友和值得信赖的临床医生的情感和实际支持。死亡发生后,这些人留下来见证这段非凡的旅程——以及他们自己的经历。
我们与兰开斯特大学的同事一起采访了许多加速自己死亡的人的家人和朋友——无论是通过安乐死(医生开致命药物),协助自杀(医生开处方,但病人自己服药),还是由病人自愿停止饮食。我们还与那些通常经历过多次加速死亡的卫生专业人员进行了交谈。
《洞察》的编辑们委托撰写长篇新闻,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合作,这些学者从事的项目旨在解决社会和科学挑战。
许多选择帮助别人加速死亡的人说,他们感到被赋予了巨大的责任。一些人将其描述为一种“荣誉”,这可能部分是出于他们帮助他人避免不必要痛苦的道德信念。
但那些与我们交谈过的人往往敏锐地意识到,别人是如何判断加速死亡的选择和促成死亡的人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会导致持久的内疚和焦虑感,使眼看着——并帮助——他们的亲密朋友或所爱的人死去所产生的痛苦更加复杂。
乔安妮和戴尔结婚近50年后,他们发现戴尔是一名退休的学校管理人员,有迹象表明他患上了痴呆症。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允许某些形式的协助死亡的美国州,但申请人必须有不到六个月的预后。
这对夫妇通过当地临终权利组织的介绍,发现了自愿停止饮食(VSED)的另一种选择。他们了解到,不喝水通常会在10-14天内导致脱水和死亡。乔安妮说,这个选择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享受美好时光的方式,同时也减轻了戴尔对未来在护理机构中与痴呆症生活多年的焦虑。“我认为这是真正让他害怕的事情之一,”她说。
乔安妮了解了哪些选择是合法的,并决定她不会把自己置于法律风险中去帮助他(VSED不受美国法律保护,通常被认为是合法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拜访戴尔的医生,他同意在VSED过程中提供药物来减少焦虑和不适。乔安妮说,当戴尔的认知能力开始衰退时,他们的决定帮助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并不是每个和我们交谈过的人都像乔安妮一样,对于被要求帮助一个所爱的人加速他们的死亡感到很舒服。斯蒂芬妮早就知道她的父亲是瑞士公民,是一个死亡权利协会的会员。她不同意他的选择,但尊重他做出选择的权利。然而,当他被诊断出患有迅速发展的癌症后宣布他打算加速死亡时,她承认她感到非常矛盾:
但是,尽管斯蒂芬妮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希望他最终会选择自然死亡,但她觉得有义务尊重父亲的意愿,帮助他调查接受安乐死的步骤。在她的一生中,她父亲多变的情绪和对控制的需求一直影响着整个家庭;这种感觉似曾相识,令人沮丧。
随着斯蒂芬妮父亲病情的恶化,他坚持控制自己的死亡时间,以及葬礼和遗产事务的所有细节。斯蒂芬妮和她的哥哥试图帮助他,尽管他们个人并不赞成安乐死。
对于玛乔丽和她的母亲来说,从决定与尊严组织一起结束生命到前往瑞士的那几个月是苦乐参半的。马乔里的母亲要求她对除直系亲属外的所有人保密。但她也需要帮助来计划这次旅行:
家人和朋友经常被要求为加速死亡提供后勤帮助,从旅行计划和组织在家护理到到药房取致命的处方。乔安妮回忆说,戴尔开始VSED时,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寻找所需的用品和护理服务——随着他的痴呆症进展,这些任务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困难:
乔安妮描述了她填满她正在收集的所有信息和表格的“大旧活页夹”。她说,当她知道自己已经掌握了这一切时,她感到非常欣慰。突然间,戴尔的痴呆症迅速恶化。在咨询了另一个接受VSED治疗的家庭后,乔安妮回忆说:
相比之下,斯蒂芬妮和她的兄弟们尊重父亲意愿的决心受到了打击,因为父亲在死亡日期上一再改变主意。在他选定的日期之前,他服用了抗生素来控制可能致命的感染,但在他计划死亡的前一天晚上,他又动摇了。
这种不确定性一直困扰着这个家庭,他们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照顾他,但却很难跟上他不断变化的情绪。进行面谈以确认她父亲的资格并确定日期的医生只从表面上看了他的决定;斯蒂芬妮告诉我们,她希望他能更深入地探讨她父亲的矛盾心理。
斯蒂芬妮和她的哥哥觉得自己必须尊重父亲的意愿,但当这些愿望再次改变时,他们感到很沮丧,最终在父亲预定约会的前一天晚上,斯蒂芬妮和她的哥哥对父亲大发脾气,并告诉他,他们不会陪伴他去世。她上床睡觉时不确定是否还能再见到他。
随着玛乔丽母亲去世日期的临近,他们订了两张往返苏黎世的机票——“以防万一”。玛乔丽把她的两个孩子留给了一个朋友,只告诉了直系亲属他们的计划。抵达苏黎世的那一天,母女俩都不说话,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马乔里回忆说,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就像《绿野仙踪》(Wizard of Oz)被换成了特艺彩色版。”
我们的受访者——以及医学伦理学家——区分加速死亡和自杀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它们的社会性更强。自杀通常是非法的,选择自杀的人往往对他们的计划和行为保密,以免别人试图阻止他们或被指控协助他们。
然而,即使是加速死亡,除了临终者最亲密的支持者之外,很少有人会提前知道这个计划。
在美国、瑞士和奥地利,个人必须自行服用药物,有时作为饮料,但更常见的是(在瑞士)通过打开一个端口进行静脉注射。停止饮食的人需要全天候的关注,因为在一到两周的时间里,他们的身体会变得虚弱。
在计划死亡之前的几周、几天和几个小时里,家人和朋友们报告了许多不同的感受,从务实到孤立到感激。没有文化脚本告诉人们如何计划他们的死亡,以及那些帮助他们的人,如何为这个场合做准备。通常情况下,疾病进展决定了时间。在戴尔的痴呆症开始迅速发展后,他和乔安妮特意选择了他的VSED开始日期,考虑到他们的家人。她解释说:
但他们也不敢等到新的一年,因为到那时戴尔可能已经失去了不吃东西的能力。相反,他们选择在12月初迅速采取行动:
在死前的几个小时,玛乔丽的母亲在苏黎世的一个住宅区,在尊严组织维护的一个像家一样的环境中见了一位医生。医生问了一些问题,以确认她明白自己的要求。对玛乔丽来说,时间停止了。
对于那些符合该组织严格要求的人,尊严组织的医生会给他们开一些混合在水中的药物。病人必须自己喝,或者能够操纵一个阀门,通过鼻胃管或静脉通道给药。这种混合物太苦了,所以在它起作用之前,首先要服用抗恶心药物,以减少病人呕吐的机会。对玛乔丽的母亲来说,这是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问题:
计划性死亡的突然性和终结性是许多家庭护理人员报告的问题。一些人描述说,他们在死前抑制悲伤,把注意力集中在病人的需求或后勤工作上;其他人则表示,他们的亲人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死去,比他们的疾病可能带来的痛苦要少得多,这让他们感到宽慰。
VSED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当病人变得虚弱和意识不清时,护理人员必须在确保死亡如期进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保持警惕,让他们保持舒适,并提醒他们不要喝酒。这可能会给亲人和健康专业人员带来压力。还有一个问题是,其他家庭成员的参与程度如何,乔安妮解释说:
家庭通常将这段时间描述为有意义但缓慢的。乔安妮晚上靠雇来的助手陪着戴尔,这样她就可以在不分散他注意力的情况下吃饭,并得到急需的睡眠。
对斯蒂芬妮来说,父亲去世的那天带来了和解。她被一个电话唤醒了,他毕竟打算把他的决定贯彻到底。当他们到达时,他为自己对控制权的要求伤害了这家人而道歉。斯蒂芬妮回忆起他对她说:“你答应过要牵着我的手!”她回答说:“我保证过,我在这里,我会留下来,所以别担心。”
斯蒂芬妮的哥哥和她父亲的女朋友道别了。现在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跟医生在一起了,医生给她父亲调了药水喝。
大约三刻钟后,她的父亲被宣布死亡。对斯蒂芬妮来说,挥之不去的不是她父亲是怎么死的,而是去那里的情感代价:
虽然像斯蒂芬妮、乔安妮和马乔里这样的人不太可能目睹不止一次的加速死亡,但一些卫生专业人员却多次遇到这种情况。目睹或促成这种死亡——或施用致命药物——的重要性在一个更倾向于保护生命而不是终结生命的领域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
海伦是比利时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的健康助理,她说她会尽力在临终前满足病人的任何要求——有一个病人要求修指甲、化妆,并帮忙穿上最喜欢的衣服。还有一次,她回忆说,在不知道这是计划中的安乐死的情况下,她帮助一个家庭度过了紧张的最后时刻:
海伦立即向这家人道歉,因为她来之前没有看病房报告。他们告诉她不要担心,她继续吃午饭。
对于许多医疗保健专业人士来说,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和几个小时里,促进这些有意义的时刻,可以缓解他们自己在知道生命即将结束时的不和谐感。所有人都告诉我们,加速的死亡从来不是“正常的”死亡,而是伴随你的死亡。安妮卡(Anika)是一名负责管理姑息治疗病房的比利时医生,她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死亡对处理死者的医生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影响:
在之后的几天和几周里,玛乔丽发现自己不仅传达了死亡的消息,还传达了方法。她的母亲给她的许多朋友写了信,让她在从瑞士回来后寄出去,以代替葬礼。
家人和朋友将分享亲人的死讯描述为一个复杂的评估过程:对方需要多少细节;他们是否会理解选择了加速死亡;是否要在讣告中公布死亡类型。一些人报告说,他们无法从不了解整个故事的朋友或家人那里得到支持。马乔里说,对她来说,缺少葬礼服务是另一个复杂的因素:
最后,就像我们采访过的许多近亲和朋友一样,玛乔丽很高兴能够支持她母亲的愿望。但她的结论是,后勤、保密和努力远远超出了一个将死之人及其家人应该组织的范围。在她母亲去世后的几年里,她开始支持改革法律,以便英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家中去世。她自豪地描述了这次竞选活动,她说:“你知道,就像,她的死将带来一些积极的东西。”
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一些受访者——特别是那些在英国秘密加速死亡的人——觉得他们无法获得亲人自然死亡的人通常可以获得的丧亲支持,因为害怕被捕。然而,尽管在他死后,对秘密的需求给一些人带来了负担,但在我们的采访中,对持久内疚的描述却很少见。相反,我们听到许多家人和朋友说,他们决定支持他们的亲人加速死亡,他们感到平静。
一个原因可能是,对加速死亡感兴趣的人倾向于只向那些会支持他们的人寻求帮助,或者至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支持他们。此外,关于加速死亡的研究往往依赖于那些想要分享自己故事的人;那些有过负面经历的人可能不太愿意讲述它们。
将协助死亡合法化的国家数量可能会增加——包括英国。大多数关于立法的辩论仍然集中在个人做出选择的权利上——但选择不是孤立做出的,有两个关键群体需要支持:医疗保健提供者和家庭。
有一种假设认为,辅助死亡将被纳入医疗保健系统。然而,尽管最近对英国医生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赞成修改法律,允许某种形式的协助自杀,但只有少数注册医生愿意直接参与管理药物。鉴于他们的不情愿,将需要替代的交付系统,以确保在加速死亡的每个阶段都有充分的审查,以确保保障和维持信任,同时减少医生对这种潜在压力事件的暴露。
对于密切参与协助死亡的家庭成员来说,这个过程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那么孤立。然而,由于决策过程中固有的保密性,处于边缘的家人和朋友在接受一个他们不参与的决定时可能会很挣扎。对他们来说,损失可能是巨大的,来自丧亲服务的支持将是重要的。
2024年2月,英国卫生和社会保健特别委员会关于协助死亡的报告承认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很容易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考虑这一点,但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在引入新的立法之前,应咨询与协助死亡有关的所有各方。
我们制作了一部短片,把许多其他参与协助死亡的人的经历带到了生活中。但我们还没有解决与保护弱势群体有关的更广泛的关切。这场辩论是微妙而深刻的,我们应该准备好倾听所有的说法。如果英国修改法律允许协助死亡,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既保护和支持请求安乐死的人,也保护朋友、家人和医护人员。
*为保护受访者身份,本文均为化名。
给你:更多来自我们的见解系列:
孤独的神话:我们分享的孤独故事揭示了为什么你不能“修复”这种非常人类的经历
生存危机:COVID患者在多长时间内帮助我们理解了失去身份认同感和生活目标是什么感觉
孤独、失落和遗憾:变老的真正感觉——新的学习
要了解新的见解文章,请加入数十万重视the Conversation基于证据的新闻的人。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作者不为任何公司或组织工作,咨询,拥有股份或从任何公司或组织获得资金,这些公司或组织将从本文中受益,并且除了他们的学术任命之外,他们没有透露任何相关的隶属关系。
为您推荐:
- 珍珠港袭击中最年长的幸存者去世,享年105岁 2025-09-14
- 协助死亡:帮助亲人的第一手故事 2025-09-14
- 帕卡工业现场,一名钢铁工人从84米高的平台上坠落,但被钢棒刺穿 2025-09-14
- 特朗普将取代莉娜·汗担任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并任命金伯利·吉尔福伊尔为希腊大使 2025-09-14
- Ziff Davis以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CNET 2025-09-14
- 梅根·马克尔和哈里王子不寻常的“不平等”关系动态解释道 2025-09-14